普光泉:择木龙(组诗)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她记忆中的雪景
她跟我说起雪。我们在火塘边,吃着烧土豆
喝着酥油茶。她的语气漫不经心
她说那时她还年轻,还没有从上河嫁下来
还喜欢踏雪。那年冬天,大雪封山
她站在自家门口看,穿着厚裙
斜靠在自家门口看雪。看那些雪花
从高得无法知晓的地方落下来,看那些落下来的
一点点白开,最后封了河面
雪从眼前堆向河的下游,到外界去
她看久了,便看见两只狗,一黄一黑
涉过藤桥河,河水几乎没有,而两只狗
走着走着便成了雪色,和它们去追的那只野兔一起
白得不见。那场雪化过后
媒婆便到来。这年冬天,她出嫁了
如今五十年了,在记忆里,那场雪
还在飘着;那两只狗,还在追着
只是那一开始就白得不起眼的野兔
模糊不清
纳尔所多河
这条生长细鲢鱼的河叫纳尔所多河
河流由11支山箐的溪流汇成
海拔、水质、水温、空气里的负氧离子
都适合细鲢鱼生长。纳尔所多河
从穿洞子起源,到雅砻江入口
共计长17.8公里。沿着河流
生息繁衍着18户人家,他们
是一个农业产生小组,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叫法
还叫产生队。前年底,他们按照就近的原则
把河段分到各家各户管理并且捕鱼
规定:不投饲料、不捕幼鱼,实行天然养殖
段与段之间,不设围栏,也就是说
鱼游到谁家那一段,就归谁家
而捕鱼时,都不越界。这17.8公里
18户人家怎么分配呢。在开会商量时,各家各户
都争着要0.8公里。大家你推我让
最后生产队长张大成一锤定音:17户人家
每家各得1公里,他家得0.8公里
纳尔所多河
在择木龙,甚至更大的范围内
逐渐成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河
细鲢鱼卖到了很远的地方
而价格高出原来的两倍
仍然供不应求
观花不遇
事实上,六年前我便来过
在整座大青山的山脉里
骑着枣红马,观看白的、淡粉红的索玛花
走马观花开,花影是那么美好
开在了记忆里。索玛花,当地人说有十多万亩
不折不扣的花海。曾经被飞机航拍
而误认为是罂粟花,是毒流山野
还会流向人间。公安人员与科学家联合
组成考察队急匆匆赶来,虚惊一场
而花更加有名。于是有了民谣似的说法——
打开择木龙的门,饿死格萨拉的人
二0一五年五月,我再去,花已无踪影
村民说,前几天下了一场雪弹子
只剩下残枝败叶了。这个夜晚
在藤桥河边的火堆旁与阿哥阿妹们喝酒
听他们唱酒歌,我的灵魂渐渐变轻,向天上飘去
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像在锻铁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锻铁
歌声里有着性感的影子——是索玛花,抑或
少女在神秘地悸动……后来
他们再次敬我,我又喝了一杯
就这杯,让我对后来的事情一概不知
如今我对面的事实是——
择木龙的门还没有打开
格萨拉的人在饥寒中过活
迷信
我爱偏执,但从来不迷信
而这次不一样了,我申明,这是首次
一涉足择木龙,我就开始迷信,如同
中了蛊。直到走出择木龙
我仍然在迷信。我迷信择木龙的山
这山原来叫做柏林山
山上有数不清的柏树,已经成材
这山,曾经被一个文人写成了百灵山
他说这样写更有诗意,便在一大段时间里
以讹传讹。几年后才改回来
我迷信择木龙的水,其源头在川洞子
从山的肚腹里一点点浸出来,逐渐成为潺潺流水
成为山沟,成为河流,向远方的金沙江而去
身体力行地验证“海纳百川”
我迷信择木龙的山水
有着天生的圣洁与诗情画意
到了这里,我不会写诗也会吟了
时间再待久一些,我不知道
还会迷信这里的什么

村庄
从红宝乡政府旁边的箐沟,以寻找源头的方式
往里面走。远远的看见大青山,一座足够仰视的山
它在风中,像一匹自西向东进发的马
有凹下去的脖子和高高昂起来的头,鬃毛飘飞
近一些,换一个角度,马变成了大象
身体灰褐色,浸泡在早晨的雾霭里,慢慢地蠕动
阳光渐渐照到了它,雾散开些,却又像一个巨大的岩石
它的身上,被树木和鲜花装饰得漂漂亮亮
诱我前往。带路的说,翻过大青山
便能够看见择木龙。择木龙是一个村庄,而原来是一个乡
如今合并到了红宝。从大青山顶往下行,像从飞机上看见云海
却依然没有见到村庄,那低洼处,是一大片乳白的雾。偶尔有树伸出头来
我在想象中断定,这村子就藏在雾中。在低洼处,在无尽的时间里面
藤桥河一年年,一代代从它身边流淌,带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去远方
下到大青山的半山腰,雾霭散开了许多,那村庄果然渐次显现
就像一幅刚刚完成的水墨画。不闻鸡鸣犬吠
在接近时,看到一处处房顶冒出袅袅炊烟
和我所见过的村庄相似。我可以想象出炊烟下面的母爱
以及琐碎轮回的生活气息
这村庄,和我生长的阿喇乡旺牛村一样亲切忧伤
在柏林山涧
我们已经进入柏林山了,这里原始林多
请大家别用火。注意跟上,千万别掉队
踩着绿油油、厚实软绵的地衣前行
负氧离子成群结队往身体的缝隙里钻
舒一口气,心便不再浮躁
四周无尘,有鸟的轻音乐——
“小点点东西”或者“这里好安静”
我终于想明白了,这里,我跟那些草木平等
我做不了一棵树木,那就安心
做一根草吧。和野草亲近
有着草命,与它们为伍。好生想想
这数十年,其实也是一瞬间
是以短暂的生命,历经一次荣枯的轮回
以后的日子,不可再琐碎,再烦恼
活着的时间极短,死后的时间又太长
也不能够蝇营狗苟过活
我想在这柏林山涧多待一些日子
让这湿润的空气,透彻我的肺腑
洗涤我那变得贪婪的心
伐薪记
在大青山的一侧,远远地听到伐木丁丁,翻过山梁走近
好大一棵树,顺山倒。风送来沉闷的嗖嗖声
递一支烟过去,交谈,得知他叫张二民
他坐在大树靠头的这一段,擦汗,抽烟,慢吞吞与我说话
倒下了,一整根还叫做树,直,桠枝还在身上发出生长的细微声音
还可以看出枝繁叶茂,和曾经的参天姿势
年轮一圈圈荡开,散发出湿润的气息,滴下淡红的体液,仿佛流血不止
白的纹理透发出褐色。张二民抽完烟,恢复了精力
去砍桠枝。他动作熟练,有条不紊。用油锯
把树按照基本均等的方式做四段锯开,在从头到尾
用斧头一段段劈开,靠头的那段先劈成两瓣,再四瓣,再八瓣
往尖上走,瓣数成双数递减。最尖的那段小,不再劈
只是断掉细而枝叶鲜活的部分。抽了三支烟,流了无数汗
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张二民完成这棵参天大树的砍伐
我问他,这树大概有多少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七十岁左右。他凭经验说出的,我相信
树变成一堆柴,这过程,仿佛是完成对一名老者的葬礼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张二民直了直腰杆,说,肚子饿了
他让整整一棵树变成的一堆柴横七竖八躺在坡上
收拾好斧头,背上八根头一个月砍伐的
已经变白变轻的柴,顺着来路踏着余晖回家。他招呼我去他家吃饭
我点点头,跟随其后

彼时,此时
彼时是二00七年,我来过一次
上大青山,喝过藤桥河的水
还在河边用原始的方法煮细鲢鱼。那美味
足以喂养记忆一辈子,回来后,写成了《阿依阿月》
此时,已是八年过后了,再来
择木龙,路比原来宽了一些
但整个地方依然没有大规模开发
一片巨大的自然生态风景区,依然
由蓝盈盈的天空滋养着,就像一位
十七八岁的笮人女子——她还是处女
待字闺中。她美妙,一尘不染,没有丝毫俗气
此时,我奢望
这次能够在我的血管里,掺和一丁点
择木龙的水土
我还奢望,这里不被那些富人
开发利用
爱上
我从远方一座叫炳草岗的城市
赶至这里。是完成一场内心的赴约
然后,我爱上了这里的藤桥河
我爱上这里旧时有过无数座藤桥
现在没有了,但我能够清晰的想象出
它们的模样,想象得出人、狗、羊
甚至牛从它们上面经过时,那摇摇晃晃
的样子。现在,桥下面的河水依然干干净净
没有遮蔽,仿佛还照见它们的影子
河水干干净净,流入各家各户的生活
也流到外面的尘世。现在,我爱上河里面的鱼
鱼不大,也不知名。却都能够自由呼吸、生长
没有受到惊扰和污染。它们喜欢这河水
带我进山的人说:这些鱼是石鲅子或者细甲鱼
它们深谙水性,喜欢嬉戏,喜欢在浅水里做爱
并不在乎有潜伏着的危险。我爱上这里
爱的理由简单而、任性
慢
到了择木龙,山好水好,便迅速把自己
像放牧一样放了进去,所有的举动
都是迫不及待的。而我的身体
又迅速慢下来,成为一个悖论
我的灵魂也跟着逐步慢下来
慢得与世隔绝,像是被一点点溶解、稀释
直抵达一种在尘世里不敢想象的孤寂
进入夜晚,出现从未有过的——
月色冷清、星星眨眼睛,却不发出
一丝一毫声音。我真想
找到另一个自己,或者随意一个
温暖、柔软的实体。相互抱团取暖
次日,太阳来到人间,是八点
八点赖床,九点起,推开窗
整个世界,仿佛比头天还要慢
面对这方山水,无法让自己快起来
只有慢,在慢的时间和空间里
我在寻找机会,想抒发一些感叹
犬吠
夜晚,择木龙的犬,总是捕风捉影地吠
那怕是睡熟了,也还睁着第三只眼睛
洞察阳间和阴间的动静
阳人过路,阴人约会
或许它们都知晓
它们会从梦境里面警醒过来
大声吠,疯狂咬
在这方山水
要是有那一夜犬不吠了
人们便无法入睡
要是哪一夜犬一直不停地吠
全部都跑出家门联合起来吠
人们也会无法入睡
凭借经验,它们能够想出
某一件大事情会在近日发生

牧羊记
李山毛,从小就喜欢屁颠屁颠跟着他爹
上山放羊。适龄,在村子里的一师一校上学
身在学校心在山中,读到三年级便辍学
他爹从羊群中挑选出两只半大羊
给他放。他爹照常放向东坡
他放向西山。各自为政
一年后,李山毛的羊由两只变成一小群
第三年,变成一大群。第四年起
他的羊开始卖的卖,杀的杀,而羊的数量
总是有增无减。到了第七年
李山毛的羊发展到了一百一十只。这年冬天
他爹老死了。他爹的一百四十只羊归他来放
总共是二百五十只。早晨,羊圈门一打开
一百四十只羊往东,一百一十只羊往西
两群羊合不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续几个早晨,他都在他爹的羊圈门前
跺跺脚,用最粗的话骂羊。骂完,还不想开门
他很想放弃这个职业,却又放不下
说话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三十一年来,一直放羊的他,在山里
几乎不见人也不见鬼,他便
跟羊说话——咩咩咩,挥挥手
羊们便欢快地跑向绿草
到了傍晚,在夕阳下,他大声咩咩咩
羊们便收拢来,围绕着他
他在那大石头上撒上盐巴,让他们舔
然后再带它们回归
作为牧羊人,他每天
就只是说了一句话——
在太阳快要落山时,他从所躺的地方
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伸个懒腰
然后对着山,对着自己说
肚子饿了

温暖
那匹山的顶子,很形象,当地人
叫它为奶头山,远看真像一只奶头
作家毛文洪说“在晨雾里更好看。”
次日我一定早起。早晨七点半,阳光初照
四周流淌着寒气。通过一句诗
我感觉到高高在上的乳房和奶头
如此温暖。就像是一个哺乳期的少妇
躺在那里,裸露出饱满的乳房
正准备把奶头喂到婴儿的嘴巴里
那奶头,挺而紫红
在这阳光穿过薄雾的早晨
我觉得在择木龙做一个心灵寒冷,并且
饥饿的孩子,是幸福的
大青山
曾经,或者说就在五十年前
它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有熊出没。也是豹、鹿、猴、野猪、香獐、小熊猫
的乐园。它们在食物链上。遵循
适者生存的原则,实际情况是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活得很好。但是
它们居安而不思危。后来,它们一群群
惨死于大炼钢铁。它们的魂魄
随着大树倒地,再随着木头落入炉膛
而失魂落魄的肉身,在林间蒸发
现在,进入这大青山,已经
找不到它们存活过的证据了,更不必
惧怕被它们攻击
偶尔发现一些朽木上有黑木耳存在,是那
黑熊的毛色,却与黑熊没有关联
五十年前发生过的大青山黑熊
伤人事件,只是以传奇的形式
在脑海里一遍遍上演
想象月亮
想象一湾月亮,距离三尺三
或者,可以再近一些。可以深入,甚至
抵达命定的传说。此刻的晖
逐渐铺满一屋清凉。我们
可以用彼此的心跳,接近春宵
装一宿的欢畅。你说过
如果身体接纳身体、灵魂遇见灵魂
两个世界便不再迷茫
有如诗意南山的初见,接下来
在现实之外,一而再,再而三激荡
抬头看看同一片天空,看看
风的蔚蓝。在想象里,与月亮的距离
已经小于三尺三

青梅
朦朦胧胧的那天,我骑着竹马
从你家那棵青梅树下经过
经过了一次,就一次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头
后来,才听说树上有青梅
在高高的枝上,在鸟巢旁边
再后来,我通过考试进入城市
从此在城市里客居
那竹马,一直养着在身体里
不愿意离开
而它渐渐老了
在山里
过长草坪,雾散了
老天下起来蒙蒙细雨。一阵阵风
是来自天国的利刃,由一位大神操纵着
斩草、刻木、割人的耳朵,发出
呼啦呼啦,嘎吱嘎吱的声音
长草坪,失去了平时的宁静与柔情
雨停后,烧篝火取暖,在亮光里面
搭建帐篷过夜。偷窥昆虫交配
想象它们单纯的爱情;想象在那些洞穴中
幼兽的身体,紧贴着母亲,通过乳香
进入温暖的梦境……我一直呆坐
透过帐篷的缝隙,寻找黯淡的星星
这个夜晚太长,如同紧跟着的一个昼
变成了夜,好比一个男子变性而来
而血肉模糊的心,依然是石头
只是时空已经错乱了,整个人间
开始摇来晃去。夜真的太长
她说,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火葬地
把羊放进山后,牧羊人
那个寡言的老头,照常转过一道弯
来到火葬地,寻找,捡拾白骨
零星散落的骨头,有些露在灰烬外面
风吹着它们,发出阵阵呻吟
他一根根,一块块捡起来,认真仔细拼凑
尽量让它们恢复人形,每拼凑出一个
便把它想象成村里的某人
像在生那样说说话,然后架柴
再烧一次。烧时,他不断添柴,嘴巴里
念念有词。他要许多天才拼凑得起一个
把张三的骨头拼给李四,把李四的
拼给张三,这是常有的事。也会把好几个人的拼
在一起。像在玩魔方。从中获得成就感
有一天下午,火葬地突然起了雾霭
把他笼罩,他迷迷糊糊靠着一个土坎上
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的血肉散失殆尽
余下的骨头被另一个人捡拾,也架在火上烧
边烧边说,我得让你完整回到土里去
醒来后,他记得,这声音
是来自村子里那个已死去多年的老巫师
山谷
过了杀人坳,便进入山谷
刚开始时,开阔,两边的岩石、悬崖
彼此遥遥相望。那是早晨走到傍晚的路程
尽管太阳由此及彼,只需要片刻。一只黑头翁
飞过,得花去五分钟左右。往里面走
越来越窄,汗水越来越多。而空气
越来越干净。离尘世也越来越远了
听到一声虫鸣。又听到几声虫鸣。再后来
有一群虫鸣。那节奏,合着
心灵间的声音。风朝着一个方向轻微响动
摇晃了树叶,光斑如同细碎的银子,被溪流淌走
两岸的岩石、悬崖在一尺一寸靠近,从谷底
望向天空,彩云在移动,有着马的形态
以及人形。我仍在蜗牛爬行,爬行
在抹汗水时,一抬头,惊见
一朵咂蜜花,在靠近谷顶的地方开了
仿佛开在天堂,又在一个梦境
一个人的河流
他说,任何一个人
都不喜欢受到压迫
有压迫便会失去基本的自由
那天早晨,她推开门,左顾右盼
然后出去
脚步很快跨越了栅栏
在青草弥漫,野花星星点点的野外
她顺着羊肠小道,乘着一股清风
向山外去。一路上
她成为一只放生的鸟
发出鸟一样舒展的声音
流下积攒了多年的泪水
开始,风不停地掀起她的衣角
她伸开双臂,衣袂飘飘
后来,雨落到山顶
淋浴树木,白茫茫一片
有一些雨顺着风赶过来了
她在风雨中
泪和雨淌在一起
渐渐地往脚跟流下去
渐渐地
形成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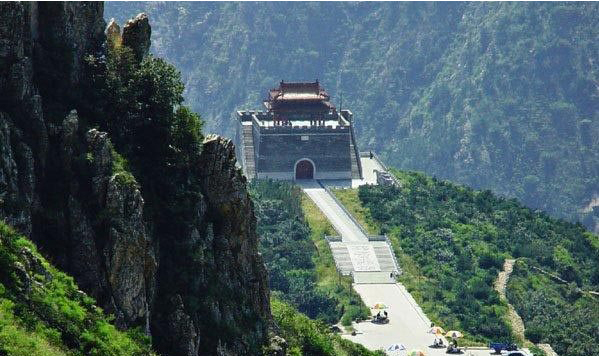
奶头山
这一方人的土话
把乳说成奶,把乳头说成奶头
把乳头山说成奶头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人都知道
奶头山。他们一生一世在奶头山脚下过活
那箐沟里流淌出来的清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是滋养他们的奶水
他们一年四季贴近这奶头山
从春天到秋天,进入冬天
再从冬天进入下一个秋天
一岁一枯荣,他们感知着奶头色彩的变化
在每一个人眼里面,从幼年
便接受了这种变化
直到把自己的一辈子过完
变化
柏林山有着很大一片原始森林
那些年,准确地说是在大炼钢铁
时代到来之前,有很多狼
它们饿了,便千方百计寻找食物
有羊吃羊,有鸡吃鸡,有狗吃狗
如果遇上人,便吃人
活着的动物和人,在它们的感知里
都一样可爱,那肉的气息
令它们垂涎三尺。都是美味佳肴
那个早上,在背水的溪流边
一匹狼,冷不丁张开血盆大口
向十五岁的阿依阿月那尚未成熟的脖子
咬了下去。阿依阿月听到极速的风声
本能地偏一下头,那血盆大口
从她左边耳朵擦下去,经过左肩
咬下了那还在发育中的左边手臂
这个事情真实地发生了
——是那些年的事情,这些年
不会再有了,但在择木龙
大人们还常常用这个故事
吓唬小孩子
让小孩子乖乖听话
赶路
从大青山赶往长草坪,途径
杀人坳,起风了。像有着无数把匕首
扎进衣服,在皮肤上划来划去
凉飕飕的,直逼内心
天黑之前,得离开杀人坳
向择木龙村进发。这是既定方案
人累极了,马行进的速度也慢了
它们的脚步不再矫健,随时都有可能
像一滩稀泥一样,四脚收拢
身体着地,不再起来
慢行不足一公里,凉飕飕的风
鼓动起雪花扑面而来,柔软的雪花
像一个个冷炸弹,投到衣服领子里面去
迅速炸开,炸碎身体的温暖
道路逐渐潮湿了。深一脚浅一脚
人和马踩在冰雪渣子上,发出连续不断
的沉闷声音。偶尔有黑头翁和麻雀飞过
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唤声被远方吸纳
是声音走漏了消息,鸟影被白雪团团围困
雪用无限的亮,把鸟影的黑藏了起来

燕窝
我常常想起择木龙的燕窝
一群燕窝,从悬崖峭壁间摘下来
一群燕子,在秋天的这个下午
流离失所。它们苍凉地叫着
飞进黄昏,不一会儿
又飞出黄昏,它们
叫得声音沙哑,像是在哭
它们,用这样的声音
不停地画着弧线,仿佛
这些弧线绕来绕去,便能够构筑起
它们原来的家园。但是,它们失望了
它们互相交头接耳
似乎在商量,怎么样度过夜晚的寒冷
到达明天。明天饱含希望
它们可以集体出去衔山草和细叶
共同吐出唾液,像别的鸟巢那样
建起自家的安乐窝,又可以
生儿育女人,享天伦之乐
作者简介:普光泉,1965年11月2日出生,彝族,大学文化。喜欢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在《民族文学》《诗刊》《星星》《大家》《诗歌报》《诗选刊》等刊物发过诗;已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文学、文化书籍16部,全部为反映攀枝花本土之作。长篇小说《一个说纳西话的人》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四川民族文学奖。长篇小说《阿依乌芝》即将出版。
2013年因写作而首位被评为攀枝花有突出贡献专家。
工作单位:攀枝花市文艺创作评论办公室
通讯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 人民街160号附4号
邮编:617000
电话:13219796511 0812-3340716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她记忆中的雪景
她跟我说起雪。我们在火塘边,吃着烧土豆
喝着酥油茶。她的语气漫不经心
她说那时她还年轻,还没有从上河嫁下来
还喜欢踏雪。那年冬天,大雪封山
她站在自家门口看,穿着厚裙
斜靠在自家门口看雪。看那些雪花
从高得无法知晓的地方落下来,看那些落下来的
一点点白开,最后封了河面
雪从眼前堆向河的下游,到外界去
她看久了,便看见两只狗,一黄一黑
涉过藤桥河,河水几乎没有,而两只狗
走着走着便成了雪色,和它们去追的那只野兔一起
白得不见。那场雪化过后
媒婆便到来。这年冬天,她出嫁了
如今五十年了,在记忆里,那场雪
还在飘着;那两只狗,还在追着
只是那一开始就白得不起眼的野兔
模糊不清
纳尔所多河
这条生长细鲢鱼的河叫纳尔所多河
河流由11支山箐的溪流汇成
海拔、水质、水温、空气里的负氧离子
都适合细鲢鱼生长。纳尔所多河
从穿洞子起源,到雅砻江入口
共计长17.8公里。沿着河流
生息繁衍着18户人家,他们
是一个农业产生小组,或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叫法
还叫产生队。前年底,他们按照就近的原则
把河段分到各家各户管理并且捕鱼
规定:不投饲料、不捕幼鱼,实行天然养殖
段与段之间,不设围栏,也就是说
鱼游到谁家那一段,就归谁家
而捕鱼时,都不越界。这17.8公里
18户人家怎么分配呢。在开会商量时,各家各户
都争着要0.8公里。大家你推我让
最后生产队长张大成一锤定音:17户人家
每家各得1公里,他家得0.8公里
纳尔所多河
在择木龙,甚至更大的范围内
逐渐成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河
细鲢鱼卖到了很远的地方
而价格高出原来的两倍
仍然供不应求
观花不遇
事实上,六年前我便来过
在整座大青山的山脉里
骑着枣红马,观看白的、淡粉红的索玛花
走马观花开,花影是那么美好
开在了记忆里。索玛花,当地人说有十多万亩
不折不扣的花海。曾经被飞机航拍
而误认为是罂粟花,是毒流山野
还会流向人间。公安人员与科学家联合
组成考察队急匆匆赶来,虚惊一场
而花更加有名。于是有了民谣似的说法——
打开择木龙的门,饿死格萨拉的人
二0一五年五月,我再去,花已无踪影
村民说,前几天下了一场雪弹子
只剩下残枝败叶了。这个夜晚
在藤桥河边的火堆旁与阿哥阿妹们喝酒
听他们唱酒歌,我的灵魂渐渐变轻,向天上飘去
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像在锻铁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锻铁
歌声里有着性感的影子——是索玛花,抑或
少女在神秘地悸动……后来
他们再次敬我,我又喝了一杯
就这杯,让我对后来的事情一概不知
如今我对面的事实是——
择木龙的门还没有打开
格萨拉的人在饥寒中过活
迷信
我爱偏执,但从来不迷信
而这次不一样了,我申明,这是首次
一涉足择木龙,我就开始迷信,如同
中了蛊。直到走出择木龙
我仍然在迷信。我迷信择木龙的山
这山原来叫做柏林山
山上有数不清的柏树,已经成材
这山,曾经被一个文人写成了百灵山
他说这样写更有诗意,便在一大段时间里
以讹传讹。几年后才改回来
我迷信择木龙的水,其源头在川洞子
从山的肚腹里一点点浸出来,逐渐成为潺潺流水
成为山沟,成为河流,向远方的金沙江而去
身体力行地验证“海纳百川”
我迷信择木龙的山水
有着天生的圣洁与诗情画意
到了这里,我不会写诗也会吟了
时间再待久一些,我不知道
还会迷信这里的什么

村庄
从红宝乡政府旁边的箐沟,以寻找源头的方式
往里面走。远远的看见大青山,一座足够仰视的山
它在风中,像一匹自西向东进发的马
有凹下去的脖子和高高昂起来的头,鬃毛飘飞
近一些,换一个角度,马变成了大象
身体灰褐色,浸泡在早晨的雾霭里,慢慢地蠕动
阳光渐渐照到了它,雾散开些,却又像一个巨大的岩石
它的身上,被树木和鲜花装饰得漂漂亮亮
诱我前往。带路的说,翻过大青山
便能够看见择木龙。择木龙是一个村庄,而原来是一个乡
如今合并到了红宝。从大青山顶往下行,像从飞机上看见云海
却依然没有见到村庄,那低洼处,是一大片乳白的雾。偶尔有树伸出头来
我在想象中断定,这村子就藏在雾中。在低洼处,在无尽的时间里面
藤桥河一年年,一代代从它身边流淌,带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去远方
下到大青山的半山腰,雾霭散开了许多,那村庄果然渐次显现
就像一幅刚刚完成的水墨画。不闻鸡鸣犬吠
在接近时,看到一处处房顶冒出袅袅炊烟
和我所见过的村庄相似。我可以想象出炊烟下面的母爱
以及琐碎轮回的生活气息
这村庄,和我生长的阿喇乡旺牛村一样亲切忧伤
在柏林山涧
我们已经进入柏林山了,这里原始林多
请大家别用火。注意跟上,千万别掉队
踩着绿油油、厚实软绵的地衣前行
负氧离子成群结队往身体的缝隙里钻
舒一口气,心便不再浮躁
四周无尘,有鸟的轻音乐——
“小点点东西”或者“这里好安静”
我终于想明白了,这里,我跟那些草木平等
我做不了一棵树木,那就安心
做一根草吧。和野草亲近
有着草命,与它们为伍。好生想想
这数十年,其实也是一瞬间
是以短暂的生命,历经一次荣枯的轮回
以后的日子,不可再琐碎,再烦恼
活着的时间极短,死后的时间又太长
也不能够蝇营狗苟过活
我想在这柏林山涧多待一些日子
让这湿润的空气,透彻我的肺腑
洗涤我那变得贪婪的心
伐薪记
在大青山的一侧,远远地听到伐木丁丁,翻过山梁走近
好大一棵树,顺山倒。风送来沉闷的嗖嗖声
递一支烟过去,交谈,得知他叫张二民
他坐在大树靠头的这一段,擦汗,抽烟,慢吞吞与我说话
倒下了,一整根还叫做树,直,桠枝还在身上发出生长的细微声音
还可以看出枝繁叶茂,和曾经的参天姿势
年轮一圈圈荡开,散发出湿润的气息,滴下淡红的体液,仿佛流血不止
白的纹理透发出褐色。张二民抽完烟,恢复了精力
去砍桠枝。他动作熟练,有条不紊。用油锯
把树按照基本均等的方式做四段锯开,在从头到尾
用斧头一段段劈开,靠头的那段先劈成两瓣,再四瓣,再八瓣
往尖上走,瓣数成双数递减。最尖的那段小,不再劈
只是断掉细而枝叶鲜活的部分。抽了三支烟,流了无数汗
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张二民完成这棵参天大树的砍伐
我问他,这树大概有多少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七十岁左右。他凭经验说出的,我相信
树变成一堆柴,这过程,仿佛是完成对一名老者的葬礼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张二民直了直腰杆,说,肚子饿了
他让整整一棵树变成的一堆柴横七竖八躺在坡上
收拾好斧头,背上八根头一个月砍伐的
已经变白变轻的柴,顺着来路踏着余晖回家。他招呼我去他家吃饭
我点点头,跟随其后

彼时,此时
彼时是二00七年,我来过一次
上大青山,喝过藤桥河的水
还在河边用原始的方法煮细鲢鱼。那美味
足以喂养记忆一辈子,回来后,写成了《阿依阿月》
此时,已是八年过后了,再来
择木龙,路比原来宽了一些
但整个地方依然没有大规模开发
一片巨大的自然生态风景区,依然
由蓝盈盈的天空滋养着,就像一位
十七八岁的笮人女子——她还是处女
待字闺中。她美妙,一尘不染,没有丝毫俗气
此时,我奢望
这次能够在我的血管里,掺和一丁点
择木龙的水土
我还奢望,这里不被那些富人
开发利用
爱上
我从远方一座叫炳草岗的城市
赶至这里。是完成一场内心的赴约
然后,我爱上了这里的藤桥河
我爱上这里旧时有过无数座藤桥
现在没有了,但我能够清晰的想象出
它们的模样,想象得出人、狗、羊
甚至牛从它们上面经过时,那摇摇晃晃
的样子。现在,桥下面的河水依然干干净净
没有遮蔽,仿佛还照见它们的影子
河水干干净净,流入各家各户的生活
也流到外面的尘世。现在,我爱上河里面的鱼
鱼不大,也不知名。却都能够自由呼吸、生长
没有受到惊扰和污染。它们喜欢这河水
带我进山的人说:这些鱼是石鲅子或者细甲鱼
它们深谙水性,喜欢嬉戏,喜欢在浅水里做爱
并不在乎有潜伏着的危险。我爱上这里
爱的理由简单而、任性
慢
到了择木龙,山好水好,便迅速把自己
像放牧一样放了进去,所有的举动
都是迫不及待的。而我的身体
又迅速慢下来,成为一个悖论
我的灵魂也跟着逐步慢下来
慢得与世隔绝,像是被一点点溶解、稀释
直抵达一种在尘世里不敢想象的孤寂
进入夜晚,出现从未有过的——
月色冷清、星星眨眼睛,却不发出
一丝一毫声音。我真想
找到另一个自己,或者随意一个
温暖、柔软的实体。相互抱团取暖
次日,太阳来到人间,是八点
八点赖床,九点起,推开窗
整个世界,仿佛比头天还要慢
面对这方山水,无法让自己快起来
只有慢,在慢的时间和空间里
我在寻找机会,想抒发一些感叹
犬吠
夜晚,择木龙的犬,总是捕风捉影地吠
那怕是睡熟了,也还睁着第三只眼睛
洞察阳间和阴间的动静
阳人过路,阴人约会
或许它们都知晓
它们会从梦境里面警醒过来
大声吠,疯狂咬
在这方山水
要是有那一夜犬不吠了
人们便无法入睡
要是哪一夜犬一直不停地吠
全部都跑出家门联合起来吠
人们也会无法入睡
凭借经验,它们能够想出
某一件大事情会在近日发生

牧羊记
李山毛,从小就喜欢屁颠屁颠跟着他爹
上山放羊。适龄,在村子里的一师一校上学
身在学校心在山中,读到三年级便辍学
他爹从羊群中挑选出两只半大羊
给他放。他爹照常放向东坡
他放向西山。各自为政
一年后,李山毛的羊由两只变成一小群
第三年,变成一大群。第四年起
他的羊开始卖的卖,杀的杀,而羊的数量
总是有增无减。到了第七年
李山毛的羊发展到了一百一十只。这年冬天
他爹老死了。他爹的一百四十只羊归他来放
总共是二百五十只。早晨,羊圈门一打开
一百四十只羊往东,一百一十只羊往西
两群羊合不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续几个早晨,他都在他爹的羊圈门前
跺跺脚,用最粗的话骂羊。骂完,还不想开门
他很想放弃这个职业,却又放不下
说话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三十一年来,一直放羊的他,在山里
几乎不见人也不见鬼,他便
跟羊说话——咩咩咩,挥挥手
羊们便欢快地跑向绿草
到了傍晚,在夕阳下,他大声咩咩咩
羊们便收拢来,围绕着他
他在那大石头上撒上盐巴,让他们舔
然后再带它们回归
作为牧羊人,他每天
就只是说了一句话——
在太阳快要落山时,他从所躺的地方
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伸个懒腰
然后对着山,对着自己说
肚子饿了

温暖
那匹山的顶子,很形象,当地人
叫它为奶头山,远看真像一只奶头
作家毛文洪说“在晨雾里更好看。”
次日我一定早起。早晨七点半,阳光初照
四周流淌着寒气。通过一句诗
我感觉到高高在上的乳房和奶头
如此温暖。就像是一个哺乳期的少妇
躺在那里,裸露出饱满的乳房
正准备把奶头喂到婴儿的嘴巴里
那奶头,挺而紫红
在这阳光穿过薄雾的早晨
我觉得在择木龙做一个心灵寒冷,并且
饥饿的孩子,是幸福的
大青山
曾经,或者说就在五十年前
它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有熊出没。也是豹、鹿、猴、野猪、香獐、小熊猫
的乐园。它们在食物链上。遵循
适者生存的原则,实际情况是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活得很好。但是
它们居安而不思危。后来,它们一群群
惨死于大炼钢铁。它们的魂魄
随着大树倒地,再随着木头落入炉膛
而失魂落魄的肉身,在林间蒸发
现在,进入这大青山,已经
找不到它们存活过的证据了,更不必
惧怕被它们攻击
偶尔发现一些朽木上有黑木耳存在,是那
黑熊的毛色,却与黑熊没有关联
五十年前发生过的大青山黑熊
伤人事件,只是以传奇的形式
在脑海里一遍遍上演
想象月亮
想象一湾月亮,距离三尺三
或者,可以再近一些。可以深入,甚至
抵达命定的传说。此刻的晖
逐渐铺满一屋清凉。我们
可以用彼此的心跳,接近春宵
装一宿的欢畅。你说过
如果身体接纳身体、灵魂遇见灵魂
两个世界便不再迷茫
有如诗意南山的初见,接下来
在现实之外,一而再,再而三激荡
抬头看看同一片天空,看看
风的蔚蓝。在想象里,与月亮的距离
已经小于三尺三

青梅
朦朦胧胧的那天,我骑着竹马
从你家那棵青梅树下经过
经过了一次,就一次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头
后来,才听说树上有青梅
在高高的枝上,在鸟巢旁边
再后来,我通过考试进入城市
从此在城市里客居
那竹马,一直养着在身体里
不愿意离开
而它渐渐老了
在山里
过长草坪,雾散了
老天下起来蒙蒙细雨。一阵阵风
是来自天国的利刃,由一位大神操纵着
斩草、刻木、割人的耳朵,发出
呼啦呼啦,嘎吱嘎吱的声音
长草坪,失去了平时的宁静与柔情
雨停后,烧篝火取暖,在亮光里面
搭建帐篷过夜。偷窥昆虫交配
想象它们单纯的爱情;想象在那些洞穴中
幼兽的身体,紧贴着母亲,通过乳香
进入温暖的梦境……我一直呆坐
透过帐篷的缝隙,寻找黯淡的星星
这个夜晚太长,如同紧跟着的一个昼
变成了夜,好比一个男子变性而来
而血肉模糊的心,依然是石头
只是时空已经错乱了,整个人间
开始摇来晃去。夜真的太长
她说,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火葬地
把羊放进山后,牧羊人
那个寡言的老头,照常转过一道弯
来到火葬地,寻找,捡拾白骨
零星散落的骨头,有些露在灰烬外面
风吹着它们,发出阵阵呻吟
他一根根,一块块捡起来,认真仔细拼凑
尽量让它们恢复人形,每拼凑出一个
便把它想象成村里的某人
像在生那样说说话,然后架柴
再烧一次。烧时,他不断添柴,嘴巴里
念念有词。他要许多天才拼凑得起一个
把张三的骨头拼给李四,把李四的
拼给张三,这是常有的事。也会把好几个人的拼
在一起。像在玩魔方。从中获得成就感
有一天下午,火葬地突然起了雾霭
把他笼罩,他迷迷糊糊靠着一个土坎上
就睡着了。在梦中,他的血肉散失殆尽
余下的骨头被另一个人捡拾,也架在火上烧
边烧边说,我得让你完整回到土里去
醒来后,他记得,这声音
是来自村子里那个已死去多年的老巫师
山谷
过了杀人坳,便进入山谷
刚开始时,开阔,两边的岩石、悬崖
彼此遥遥相望。那是早晨走到傍晚的路程
尽管太阳由此及彼,只需要片刻。一只黑头翁
飞过,得花去五分钟左右。往里面走
越来越窄,汗水越来越多。而空气
越来越干净。离尘世也越来越远了
听到一声虫鸣。又听到几声虫鸣。再后来
有一群虫鸣。那节奏,合着
心灵间的声音。风朝着一个方向轻微响动
摇晃了树叶,光斑如同细碎的银子,被溪流淌走
两岸的岩石、悬崖在一尺一寸靠近,从谷底
望向天空,彩云在移动,有着马的形态
以及人形。我仍在蜗牛爬行,爬行
在抹汗水时,一抬头,惊见
一朵咂蜜花,在靠近谷顶的地方开了
仿佛开在天堂,又在一个梦境
一个人的河流
他说,任何一个人
都不喜欢受到压迫
有压迫便会失去基本的自由
那天早晨,她推开门,左顾右盼
然后出去
脚步很快跨越了栅栏
在青草弥漫,野花星星点点的野外
她顺着羊肠小道,乘着一股清风
向山外去。一路上
她成为一只放生的鸟
发出鸟一样舒展的声音
流下积攒了多年的泪水
开始,风不停地掀起她的衣角
她伸开双臂,衣袂飘飘
后来,雨落到山顶
淋浴树木,白茫茫一片
有一些雨顺着风赶过来了
她在风雨中
泪和雨淌在一起
渐渐地往脚跟流下去
渐渐地
形成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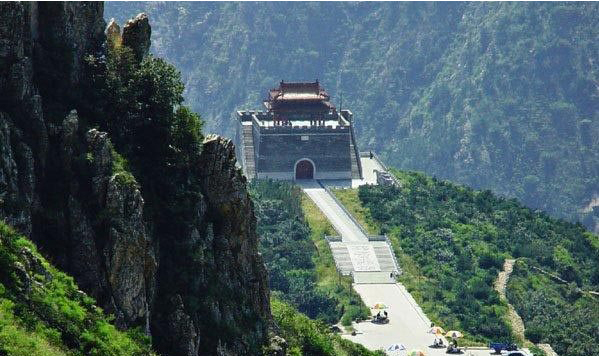
奶头山
这一方人的土话
把乳说成奶,把乳头说成奶头
把乳头山说成奶头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人都知道
奶头山。他们一生一世在奶头山脚下过活
那箐沟里流淌出来的清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是滋养他们的奶水
他们一年四季贴近这奶头山
从春天到秋天,进入冬天
再从冬天进入下一个秋天
一岁一枯荣,他们感知着奶头色彩的变化
在每一个人眼里面,从幼年
便接受了这种变化
直到把自己的一辈子过完
变化
柏林山有着很大一片原始森林
那些年,准确地说是在大炼钢铁
时代到来之前,有很多狼
它们饿了,便千方百计寻找食物
有羊吃羊,有鸡吃鸡,有狗吃狗
如果遇上人,便吃人
活着的动物和人,在它们的感知里
都一样可爱,那肉的气息
令它们垂涎三尺。都是美味佳肴
那个早上,在背水的溪流边
一匹狼,冷不丁张开血盆大口
向十五岁的阿依阿月那尚未成熟的脖子
咬了下去。阿依阿月听到极速的风声
本能地偏一下头,那血盆大口
从她左边耳朵擦下去,经过左肩
咬下了那还在发育中的左边手臂
这个事情真实地发生了
——是那些年的事情,这些年
不会再有了,但在择木龙
大人们还常常用这个故事
吓唬小孩子
让小孩子乖乖听话
赶路
从大青山赶往长草坪,途径
杀人坳,起风了。像有着无数把匕首
扎进衣服,在皮肤上划来划去
凉飕飕的,直逼内心
天黑之前,得离开杀人坳
向择木龙村进发。这是既定方案
人累极了,马行进的速度也慢了
它们的脚步不再矫健,随时都有可能
像一滩稀泥一样,四脚收拢
身体着地,不再起来
慢行不足一公里,凉飕飕的风
鼓动起雪花扑面而来,柔软的雪花
像一个个冷炸弹,投到衣服领子里面去
迅速炸开,炸碎身体的温暖
道路逐渐潮湿了。深一脚浅一脚
人和马踩在冰雪渣子上,发出连续不断
的沉闷声音。偶尔有黑头翁和麻雀飞过
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唤声被远方吸纳
是声音走漏了消息,鸟影被白雪团团围困
雪用无限的亮,把鸟影的黑藏了起来

燕窝
我常常想起择木龙的燕窝
一群燕窝,从悬崖峭壁间摘下来
一群燕子,在秋天的这个下午
流离失所。它们苍凉地叫着
飞进黄昏,不一会儿
又飞出黄昏,它们
叫得声音沙哑,像是在哭
它们,用这样的声音
不停地画着弧线,仿佛
这些弧线绕来绕去,便能够构筑起
它们原来的家园。但是,它们失望了
它们互相交头接耳
似乎在商量,怎么样度过夜晚的寒冷
到达明天。明天饱含希望
它们可以集体出去衔山草和细叶
共同吐出唾液,像别的鸟巢那样
建起自家的安乐窝,又可以
生儿育女人,享天伦之乐
作者简介:普光泉,1965年11月2日出生,彝族,大学文化。喜欢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在《民族文学》《诗刊》《星星》《大家》《诗歌报》《诗选刊》等刊物发过诗;已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文学、文化书籍16部,全部为反映攀枝花本土之作。长篇小说《一个说纳西话的人》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四川民族文学奖。长篇小说《阿依乌芝》即将出版。
2013年因写作而首位被评为攀枝花有突出贡献专家。
工作单位:攀枝花市文艺创作评论办公室
通讯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炳草岗 人民街160号附4号
邮编:617000
电话:13219796511 0812-3340716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 Recommendation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
/ Reading list
- 1 石里:烧灼的柔情(组诗)
- 2 加主布哈:十夜拾语(长诗)
- 3 李小麦诗歌十首
- 4 秦宏:第五个季节(外7首)
- 5 苏文权诗歌选
- 6 毛明友:乌蒙神鹰(长篇诗小说)
- 7 龙子元布长诗系列:乐山印记
- 8 发星长诗: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
- 9 吉木五乃《青春·记忆》节选
- 10 毛小兵诗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