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永远的女儿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

阿果小时候躺在被窝里睡不着时,常常会想到,如果我死了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思来想去,也无非是抬我去大吃一顿我最想吃的饼干罢了。”长大后,这种想法竟变成了她原谅别人的一种方式了。“一想到有一天我会死,就安慰自己,算了,没什么意义。我很会用这事来化解生活中遇到的烦恼,而且特管用。” 
“我家离上学的地方很远,有十几公里吧。远处有青山,身边有各种野果子,可以边吃边玩,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从来就不觉得累。”上初中时,由于是学校的广播员,每天清晨都要播音,阿果只能住校了。“可能是因为独自生活,没人说没人管吧,那时我的性格十分外向,唱歌跳舞一个人可以表演两个小时。”

有一年,电影《奴隶的女儿》摄制组来学校招小演员。“一个老红军给我们讲他被地主折磨的故事,我是哭得最惨的一个。那时我还不知道是招演员。”导演见阿果感情饱满,就让她随剧组到成都拍戏去了。阿果的演员梦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从此,阿果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是自己编台词,自己感动自己。”可高考那年,阿果还是阴差阳错地考进了西南民族学院的政治系。大学毕业后,阿果竟被分到了重庆市话剧团。“可惜,那几年我一部话剧没演成,却上了几十部电视剧的戏。”阿果不喜欢被人挑来选去的感觉,也就淡化了儿时的演员梦。后来,成都有线电视台招聘,阿果考上了,成为影视类栏目的主持人。一年后又去了四川电视台的“黄金十频道”。正当阿果“如日中天”时,她却毅然选择了北上。很多人为她感到惋惜,认为“年轻人应该先守住这个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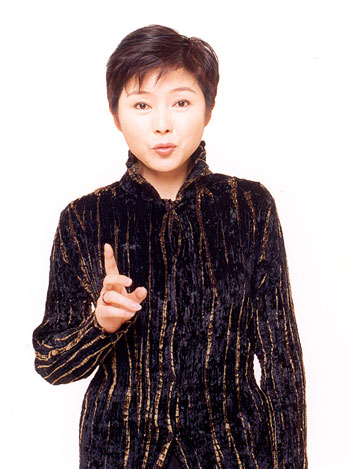
阿果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觉得做主持人应该有更大的舞台,我想去做更多的事,完全没有顾虑,况且,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只要肯勤奋努力,别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尽管离开家乡许多年了,但阿果仍然对大凉山充满了感情。今年是西南民族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庆典,要求每个人说一句话。阿果认真地说:“当我们实际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的心理距离反而越来越近了。”这就是阿果故乡情的真实写照。
身为彝族人的后代,阿果对族别的意识并不很明细。“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不太一样。虽然我的亲戚都是彝族人,但我接受的是汉族教育,同学也大多是汉族人。”工作以后,因为名字,族别才强化了阿果的感觉,与周围的人不太一样。“其实,我对自己民族了解挺少的,很肤浅的,只有直觉,但不了解本质、历史、文化,从彝族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真的很遗憾。” 
阿果很喜欢听来自家乡的“山鹰”组合的一首叫《忧郁的母语》的歌。“这首歌唱出了彝族悠久的历史和曾经灿烂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许多好的东西在逐渐流失,你也许能看到,但无法改变。这种感觉很强烈,不想找回一些东西,想去强化它,但自己这时显得很无力。这方面我常怀着一种老人的心态。平时我大多穿汉族的衣服,但逢年过节我会穿彝族的民族服装。这种血缘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能割舍的。”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
母亲是个心态很好的人。退休后,就忙着组织合唱团、秧歌队,还学会了跳交谊舞,画山水画。阿果家里的冰箱上有一张母亲敲鼓的照片。“每次一开冰箱时,就有一种温暖”。母亲去年来北京做胆结石手术,阿果一边守着母亲一边趴在床边写工作总结。母亲高兴地告诉别人,说有这样一个女儿太自豪了,工作不耽误,同时又能很好地照顾我。如果阿果下班回家晚,母亲就不睡觉,等着听阿果的脚步声。“有时我做节目似乎是为了母亲。她也许只看我的胖瘦和气色,而不关心节目内容,然后通过我在电视中的形象判断我是否遇到问题了。我在母亲面前,从来没有拘束的感觉。我想我是幸运的,有这么好的母亲和外婆。”

阿果小时候躺在被窝里睡不着时,常常会想到,如果我死了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思来想去,也无非是抬我去大吃一顿我最想吃的饼干罢了。”长大后,这种想法竟变成了她原谅别人的一种方式了。“一想到有一天我会死,就安慰自己,算了,没什么意义。我很会用这事来化解生活中遇到的烦恼,而且特管用。”

“我家离上学的地方很远,有十几公里吧。远处有青山,身边有各种野果子,可以边吃边玩,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从来就不觉得累。”上初中时,由于是学校的广播员,每天清晨都要播音,阿果只能住校了。“可能是因为独自生活,没人说没人管吧,那时我的性格十分外向,唱歌跳舞一个人可以表演两个小时。”

有一年,电影《奴隶的女儿》摄制组来学校招小演员。“一个老红军给我们讲他被地主折磨的故事,我是哭得最惨的一个。那时我还不知道是招演员。”导演见阿果感情饱满,就让她随剧组到成都拍戏去了。阿果的演员梦就是那时候落下的。从此,阿果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是自己编台词,自己感动自己。”可高考那年,阿果还是阴差阳错地考进了西南民族学院的政治系。大学毕业后,阿果竟被分到了重庆市话剧团。“可惜,那几年我一部话剧没演成,却上了几十部电视剧的戏。”阿果不喜欢被人挑来选去的感觉,也就淡化了儿时的演员梦。后来,成都有线电视台招聘,阿果考上了,成为影视类栏目的主持人。一年后又去了四川电视台的“黄金十频道”。正当阿果“如日中天”时,她却毅然选择了北上。很多人为她感到惋惜,认为“年轻人应该先守住这个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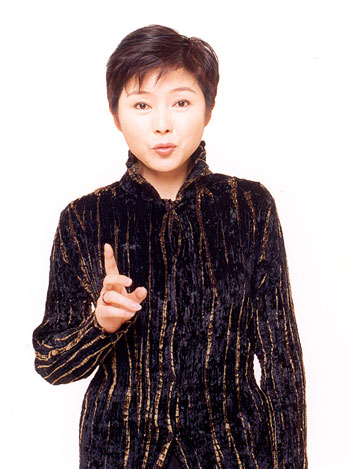
阿果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觉得做主持人应该有更大的舞台,我想去做更多的事,完全没有顾虑,况且,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只要肯勤奋努力,别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尽管离开家乡许多年了,但阿果仍然对大凉山充满了感情。今年是西南民族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庆典,要求每个人说一句话。阿果认真地说:“当我们实际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的心理距离反而越来越近了。”这就是阿果故乡情的真实写照。
身为彝族人的后代,阿果对族别的意识并不很明细。“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不太一样。虽然我的亲戚都是彝族人,但我接受的是汉族教育,同学也大多是汉族人。”工作以后,因为名字,族别才强化了阿果的感觉,与周围的人不太一样。“其实,我对自己民族了解挺少的,很肤浅的,只有直觉,但不了解本质、历史、文化,从彝族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真的很遗憾。”

阿果很喜欢听来自家乡的“山鹰”组合的一首叫《忧郁的母语》的歌。“这首歌唱出了彝族悠久的历史和曾经灿烂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许多好的东西在逐渐流失,你也许能看到,但无法改变。这种感觉很强烈,不想找回一些东西,想去强化它,但自己这时显得很无力。这方面我常怀着一种老人的心态。平时我大多穿汉族的衣服,但逢年过节我会穿彝族的民族服装。这种血缘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能割舍的。”



 / Recommendation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