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罪文化研究
彝族人-网是创建最早,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彝族文化网站。网站的目标,是构建彝族文化核心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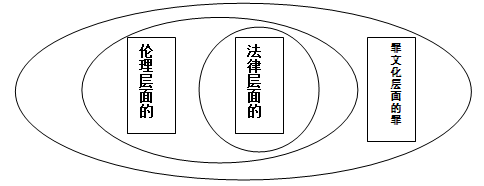
彝族人-网是创建最早,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彝族文化网站。网站的目标,是构建彝族文化核心数据库。
摘 要:罪文化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彝族罪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出现导源于彝族先民对惩罚的恐惧。从哲学角度看,彝族罪文化又具有实存论的意义。罪文化兼收外来文化因素,逐渐孕育出彝族伦理思想。彝族罪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传承,在彝族社会中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
关键词:罪文化;罪意识;解罪;伦理;社会控制
罪文化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在古典人类学时期的著作中有详尽的描写。《原始文化》中记录的蒙昧人视动物的生死如人的生死,在猎杀动物前要向他们赠以礼物并请求得到宽恕。北美印第安人、北海道的阿依努人以及柬埔寨人对他们将要杀死的动物充满了敬畏和罪感,并试图通过各种仪式解罪或赎罪。[1](P382)相似的事例也存在于印度南部尼格里山区的巴达加人的葬礼上。他们在丧葬仪式上将死者生前的罪转移到一头牛犊身上,借此使死者的灵魂得到洗礼,以便顺利地皈依上帝。巴达加人以极其庄重的仪式在祭司的主持下共同回顾亡者的罪行,在他们的观念中,微小至杀死一条蛇都是罪。[2](P768)现代宗教产生以后,罪意识更是以信仰的形式得到强化。基督教认为人类始祖受到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从而对上帝犯了原罪。同时,人类还违背了上帝的禁令,犯了不同程度的本罪。[3](P30-32)在保罗那里,人的罪在于“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前者犯了骄傲之罪,后者犯了纵欲之罪。[4](P4)佛教的因果轮回论阐释了一种对人性邪恶的强烈谴责,并建构出阴森恐怖的地狱来警告世人弃恶从善。云南基诺族认为每年耕地前砍倒树会得罪树神,全寨人以一天不下地干活的方式向树神道歉。[5](P126-128) 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对彝族罪文化作粗浅的探讨。
彝族罪文化溯源
有关彝族罪文化的文献记载最早可朔源至举奢哲写作的《彝族诗文论》。他在《彝族诗文论•经书的写法》中要求毕摩撰写经书时应当记下亡者生前所犯下的罪。必须阐明的是,彝族人观念中的罪并非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罪,亦非法律范畴内的罪。从语源学上来看,伦字的本义是“辈”的意思,引申后有群、类、比、序等含义。《孟子》一书强调的人伦,是指当时人们之间的各种道德关系及其道德标准。《礼记•乐记》载:“乐者,通伦理者也。”这里的伦理一词,既有伦类、条理的一般意义,又指当时的道德关系。在西方,英语或俄语的伦理或伦理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伊索思一词,含有风尚、习俗、品质、德性等意思。[6](P395)一般来说,中西伦理学意义上的罪是指社会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的败坏。彝语中的罪则兼有错、迷等含义。[7](P155)伦理学意义上的“罪”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基督教语境下的“罪”侧重指人神关系的破裂;彝族先民观念中的“罪”则侧重指人对天、山、河流、祖先及其对神灵的不敬,也指对动物、植物的伤害,甚至延伸到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愧疚和给他人造成的麻烦,这是一种原始的罪意识,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泛罪意识。它反映了主体对客体、自我对它者的普遍的罪感。《彝族诗文论•经书的写法》写道:“亡者(笔者加)长到中年后,中年的时候,箐中万物呀,万物他伤害,伤害过没有?如果伤害过,他就有罪过,有罪就悔罪。”[8](P41)这种罪意识在《百解经》中有直观的反映。毕摩为亡者解罪时要列出亡者随年龄增长所犯下的罪过,并施行巫术为其解罪。云南一部《百解经》[9](P113-119)所列的罪见下表:
| 范围 | 具体罪恶 |
| 家庭 | 使爹娘辛劳 哥弟打架 兄弟争家产 不敬亲戚 不治爹娘病 不孝爹娘 骂儿媳 打儿孙 教导婆媳不周 在床上屙屎、撒尿 吃白米不吃杂粮 只讲阴间话 寿终眼望天 去世背睡地 尸体有臭味 死时磨累人 |
| 社会 | 淫念(淫人妻、乱人夫、老不正经) 不敬老人 买卖挣钱 打太医 骂巫师 指路不明白 不修路 不搭桥 |
| 动物、昆虫及植物 | 不喂耕牛 加重耕牛负担 不爱惜秧苗 杀牲(猪、羊) 骂蝗虫 踏虫蚁 伤鸟 猎兽 |
| 神灵 | 不敬灶君 不祭龙 骂雷神 骂闪娘 骂风 骂天 骂地 |
| 祖先 | 上坟不压纸 只接不送 不修坟 不献祖 不洗灵位、灵牌 不换净水 不戴孝 不跪拜 埋尸不周 灵堂不点灯 献饭不恭敬 烧纸烧不尽 |
彝族的罪意识作为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是后期伦理思想的母体。与罪意识共生的是悔罪意识,悔罪意识又演化出解罪∕替罪的巫术仪式。这一文化现象也广见于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奥斯蒂亚克人将杀死熊的罪转给俄罗斯人;[2](P740)受霍乱困扰的巴尔人、马兰人将一只山羊或水牛赶出村庄,让它们为公众替罪;[2](P799)奥尼沙城的罪人企图将纵火、盗窃、奸淫、巫蛊等罪转到一个集体凑钱买来的病人身上。[2](P805)彝族先贤举奢哲教诲彝族人通过杀猪和杀羊来替死者抵罪。他说:“假如罪大的,罪大消不掉,就用猪和羊,杀来抵罪过。这样一来呀,死者能安心,生者过得好,死者罪抵消。”[8](P41)彝族原始巫术中的禳解巫术是用来解除罪恶、灾祸的巫术。“彝族人凡遇家运不顺,械斗失利,疾病缠身,庄稼遭灾,牲畜瘟疫,婚丧事完结,以及认为发生不详之兆,都要请毕摩禳解,举行各种不同的巫术仪式。”[10](P7)云南彝区传说中的古代彝人张孝为救治母亲而窃皇宫之物凤凰心脏,皇帝论其罪当诛。张孝之弟张礼力争为兄长赴死,皇帝受兄弟二人孝义感动,让稻草人负罪而死,替张孝罪。[10](P61)云南楚雄的毕摩则以念诵《百解经》和举行巫术仪式为亡者解罪。罪意识是罪文化的内核,消除罪恶的巫术则是罪文化的外壳。
恐惧心理与实存论:彝族罪文化的发生机制
彝族先民的罪文化直接导源于彝族先民的恐惧感:恐惧罪带来的惩罚。彝族认为,人生中的灾祸、瘟疫、乃至死亡都是因罪而遭到惩罚,罪与惩罚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折叠濮》写道:“祖辈多积善,后辈得好报;父辈行善礼,子辈得安详。你要知道啊!积善会成德,行恶生恶仇。”[11](P5)彝族神话《洪水淹天》认为,独眼世界和直眼世界的人不敬祖,不敬老人,不抚养鰥寡,不救济穷人,懒惰,抢窃,偷盗,这一系列的罪恶激怒了最高存在物,最高存在物让各种灾害降临人间,直至以洪水淹灭人间。[9](P88-102)《赊_(穴、豆,上下结构,笔者加)榷濮•叙祖白》描写的直眼时代与独眼时代因人们蒙昧、蛮横而世道混乱,生命难保。人犯下罪行不仅生前会遭到惩罚,死后仍不得安宁。[12](P101)彝族毕摩认为,为匪为盗而死,乱伦而死的人是不能进祭场被超度的。[13](P39)彝族人对惩罚的恐惧被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史诗、故事、以及日常行为禁忌所强化。恐惧衍生出对罪恶的强烈谴责和对善的热烈追求。E.云格尔说:“恐惧与怯懦截然不同。……人在恐惧之中为他的现实之未来焦虑。所以,焦虑与人对希望的依赖性密切相关。[14](P115)彝族先民内心的恐惧、焦虑在其躯体内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于是需要寻找替代行为来维系平衡,这一行为就是解罪∕赎罪巫术。彝族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向崇拜对象寻求庇护的心理。以祖先崇拜为例。毕摩教是在万物有灵观影响下形成的原始宗教,多神崇拜是其显著特征。然而,彝族在崇拜多神的同时,又侧重于祖先崇拜,祖先是彝族人最可靠、最亲近的保护神。彝族《指路经》旨在指引祖先的亡灵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祖先在亡灵世界形成了一个力量巨大的庇护群体,因而彝族的祭祖行为意义重大:“年年祭祖,祖灵保儿孙清吉,保六蓄兴旺,五谷丰登。” [15](P165-166)受祖先崇拜的影响,不敬祖先被视为重罪。这一现象在当代彝族地区仍有遗存。笔者在云南楚雄彝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收集到一个祖灵降罪的事例。男主人在七月半(祭祖期间)不小心于自家楼房上踩死了一条黑蛇,全家人即认为黑蛇是祖灵(男主人的已故的母亲)回家与家人团圆。全家人都为此事恐惧、不安,并把一年中的家运不顺(猪瘟、鸡瘟、人生疾病)归因于开罪祖灵,最后只得请朵觋(毕摩的当地俗称)施行巫术,解罪消灾。全家人经历了犯下罪行(踩死黑蛇)→ 遭受惩罚(瘟疫、疾病)→ 解罪(朵觋施行巫术)这一过程。
从哲学角度来看,彝族罪文化的出现有着实存论的意义。实存主义认为一切实存中的事物都具有有限性。实存中的人都存在于自由与有限、可能性与事实性之间。死亡使人类饱受荒诞和虚无的威胁。死亡这一无人可以幸免的结局使人类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产生了实存论上的忧惧。彝族神话《天神定生死》反应出一种对永生的向往:“远古的人们,长寿不会死。从来不兴死,老了蜕去皮,嫩皮又出来。” [9](P103-108)这则神话中,人和其它万物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得罪了天神。
对死亡的恐惧带来了灵魂不朽观和对生的重视。举奢哲记载道,彝族先民们“人死知流泪,丧葬心伤悲。” [8](P39)彝族先民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沉痛的悼念”,开始写经书,经书记写亡者生前罪行的惯例发端于此。E•云格尔说:“罪要求趋向于无关系,它造成关系破裂。死正是趋向于无关系这种要求的结果。就此而言,人类学上的死不仅存在于人命终结之处,而且作为实际可能存在于趋于无关系的要求之中。” [14](P69)人既然是一种有限存在,他就不能维护自由与有限之间的平衡。彝族先民只有对天地万物开放,才能获得对自身实存的支援。这种开放表现为自身与他物之间的一种神秘性的互渗。罪趋向于无关系,罪意识与悔罪意识则趋向于有关系。彝族罪的观念之所以延伸到如此宽泛的领域,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对自身实存的支援。原始人知道自身知识的限度(人的有限性),在自身知识的限度之外,他们相信存在着一种力量,巫术则用于应对这种不可知的力量。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即使是文化较低的民族,亦是完全明了知识的力量,并且知道知识的限度,也就是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科学所无能为力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亦只有在这一领域内,他们疑心有另一种在那支配着的力量。巫术绝不是原始科学。它的发生是出于他们认识到科学有它的限度,及人类的聪明、人类的技术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巫术在它的夸大性,在它的‘万能性’上,和感情冲动,白天做梦以及强烈而不能实现的欲望是相似的。” [16](P62)彝族毕摩念《百解经》和施行解罪仪式,是希望巫术能消除罪恶,试图超越人的有限性。
彝族罪文化先于伦理思想而产生,罪文化孕育出伦理思想。彝族罪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在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强大辐射之下,毕摩从儒学、道教、佛教诸多文化中改造吸收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文化要素,将他们与彝族传统文化有机地融汇于一体,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毕摩文化。” [10](P17)彝族的一些《指路经》明显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有了阎王、地狱、太上老君的出现。[9](P120-132)彝族现代意义上的伦理思想产生于阶级社会,它是以罪文化为母体,吸收了外来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而形成的。彝族伦理教育经典《玛木特依》的教育对象有“兹”(君)、“莫”(臣)、“呗”、“师”、“格”(匠)、“着”(民)的区分,教育内容以“礼”、“亲”、“义”、“序”、“名”、“信”、“善”、“忠孝”等八大内容为中心。[17](P217-223)流传于彝区的《道理经》有崇拜天地等原始罪文化的遗存,也出现了忠君守法的伦理思想。[18](P114-123)罪文化层面的“罪”靠恐惧来遏制,伦理层面的罪由公众舆论来监督,法律层面的罪则由国家强制力来制裁。三种不同层面的罪用逻辑学上的欧拉图示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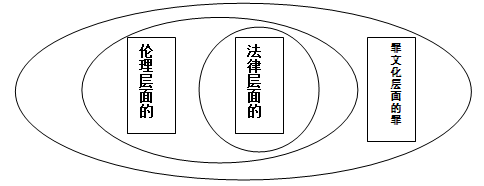
泰勒说:“全世界各种宗教,通过一个万物有灵原理而结合在一起,由于介入了道德成分,他们分化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低级体系,其最佳成果就是向人们提供孩童般天真纯朴的自然哲学;另一类是高级信仰,正当神圣的法律牢固地树立在其基础之上,它还激励人们的责任心和慈爱心,假如我们思考一下这一事件,它就将有助于理解:伦理的影响,比起哲学说教来说,对于宗教的效力是多么的巨大。” [1](P687-688)泰勒所谓的“天真纯朴的自然哲学”,彝族罪文化就是一例。
社会控制:彝族罪文化的功能
彝族罪文化作为一种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并且在重新诠释时被再度重构,因而呈现出连续性的状态。[19](P45-53)按照功能派的理论,文化是因为直接或简接地满足人类的生理或心理需要而存在的。罪文化一方面起到对恐惧的安抚作用,同时又发挥了社会控制的功能。崇拜自然万物,以伤害万物为罪,对猎杀动物,砍伐森林,污染水源等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例如,云南禄劝的彝族认为,猎杀野生动物是有罪的,因为野生动物属于山神。彝族“孝”的观念受到祖先崇拜的影响,因为父母亡故之后,就成为了祖灵,不敬父母之罪即是不敬未来祖灵之罪。伴随毕摩为亡者解罪的巫术行为,罪文化以族人对他人之死的直接体验在族人的集体记忆中得到传承。A•哈恩(A•Hahn)的研究证实,简单的社会与死多有直接联系。[14](P20)死亡对彝族先民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即便在现在的彝区,死亡从来都是整个家支成员共同的大事。毕摩主持的丧葬仪式形成了一个群体参与的精神场域,这是一个毕摩解罪、氏族成员悔罪的精神域场。庄重的仪式氛围激发出对罪的悔悟、谴责,同时衍生出对善的向往。他们相信有超自然力量在监视自己的行为,并会对有罪之人加以惩罚。这时,“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16](P86)与罪相关的看法和行为告诉人们应该遵守的规则,这种认知对彝族社会产生一种普遍的约束力量,并由此提供向善的动力,使人们遵守行为规范。
注释:
[1](英)泰勒(Tylor)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英)弗雷泽(Frazer)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 ﹒北京:大众科学出版社,1998.
[3](芬)罗明嘉,(芬)黄保罗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圣经﹒罗马书1:25.
[5]郑晓云﹒最后的长房——基诺族父系大家庭与文化变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宋希人等编﹒伦理学大辞典[M] ﹒长春:人民出版社,1989.
[7]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彝汉字典[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8]举奢哲等著﹒康健等编﹒彝族诗文论[C]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9]者厚培收集﹒楚雄民族宗教事务局编﹒三女找太阳——楚雄民族民间文学集[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1]杨家福释读﹒罗希吾戈等译著﹒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12]朱琚元等﹒赊_(穴、豆,上下结构,笔者加)榷濮,叙祖白[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13]达尔.吉克.则伙﹒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14] 云格尔(Jungel,E.)著﹒林克译﹒死论[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
[15]云南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云南彝族歌谣集成[M]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16](英)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7]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彝文文献研究[C]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18]师有福主编﹒彝族古籍研究文集[C]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19]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中国哲学史[J] ﹒2001,(1).
作者简介:李世武,男,彝族,1984年生,云南楚雄人,文学学士,民俗学硕士,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人类学。在《民族文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民族艺术》、《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洱海村》(专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文学卷》(合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论文获云南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稿件来源:《彝博通讯》 第25期)



 / Recommendation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
/ Reading list